文/古松崇志(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編按:以南方中原為根據地的農耕王朝,與以北方草原為根據地的游牧王朝,生存手段相異的兩大勢力,歷經千年的對峙,相互爭奪霸權。然而在過去中西方的歷史論述中,游牧民族總是被置於邊緣。在聯經最新出版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中譯本第三冊《草原的稱霸》中,日本學者古松崇志大膽地重新定位了游牧民族在內亞地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並且透過審視這些游牧民族及其所創建的國家和王朝,以及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聯,描繪出多種民族往來交流之多元世界的歷史。
本文摘錄自《岩波新書 · 中國的歷史3:草原的稱霸》之序章〈歐亞東方史及游牧王朝〉,標題為編者擬。
一、內亞的騎馬游牧民族
何謂內亞地區
當我們眺望歐亞大陸衛星圖時,可以看出從大陸中央部分一直到西南部分為止延伸著缺乏地表植被的土壤地帶,這塊土色的區域即是沙漠或乾草原(steppe)遍布的廣大乾燥地帶。
在此乾燥的歐亞大陸內陸部分,近年來人們著眼於生活此地區人們的生活與文化共通性,將此區統括稱為內亞並逐漸固定下來。內亞區域廣大,想要掌握此地自然與人們生活樣態時,將其二分為北方草原地帶及南方沙漠地帶會更容易理解。
乾草原(steppe)的草原地帶大約在北緯45度至50度間向東西延伸,東起大興安嶺山脈東麓,經蒙古高原、準噶爾盆地、哈薩克草原、南俄草原(往昔的欽察草原),向西延伸至東歐匈牙利平原為止。此地帶草本植物較為茂盛,屬於適合游牧的自然環境。職是之故,歷史上北方草原地帶長期皆為游牧民族的生活天地。
稍微偏南的北緯40度左右,大致年均降雨量不足200公釐,東起戈壁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沙漠地帶向東西延伸。極度乾燥的沙漠區域不適人居,但高山山脈周遭因保有河川、泉水、地下水等水源,出現散布各處的綠洲。這些綠洲地帶自古即栽培小麥,進行灌溉農耕與畜牧,形成聚落或城市。
沙漠地帶的南側依然延伸著乾燥地帶,在帕米爾高原以東、塔里木盆地東南、世界的屋脊喜馬拉雅山脈以北,橫亙著既高又廣的西藏高原。西藏因乾燥導致許多地方屬於不毛地帶,但部分沿河谷地則為適合農耕、定居的場所。草原及半沙漠則可進行游牧。帕米爾高原西側的西亞北部則連綿著乾燥高原,雖然乾燥,但山間谷地、山麓等可確保水源處仍有可能進行灌溉農耕。西亞為既適合農耕也適合畜牧的區域,歷史上屢屢可見農耕居民與游牧民族共存的狀況。
發源自乾燥地帶的農耕與畜牧
如此一來,內亞乾燥地帶的傳統生活方式可以大致區分為草原上的游牧及綠洲區的定居農耕兩類,而它們又形成了什麼樣的歷史?
至西元前10000年為止,人類已經透過狩獵採集取得食糧,接著人們開始在西亞的「肥沃新月地帶」(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至敘利亞、巴勒斯坦之間區域)栽培小麥、豆類,且畜養綿羊、山羊、豬、牛,展開農耕、畜牧生活。附隨於農耕的畜牧最早在過著移動生活的狩獵採集族群中出現。據推測,西亞應該並存著農耕畜牧民與狩獵畜牧民,西元前5500年左右,西亞草原地帶隨氣候暖化導致乾燥加劇,導致邊移動邊進行畜牧的人們出現。游牧自此拉開序幕。
源於西亞的小麥農耕與綿羊畜牧在西元前6000至5000年傳播至中亞一帶,但最初普遍都過著定居生活。此時期地球氣候較今日更為溫暖、濕潤,內亞北部擁有茂密的闊葉林。接著西元前2500年左右起,隨著氣候乾燥化,此區域逐漸轉變為與今日相似的草原、半沙漠區域,形成了連接歐亞東西的草原地帶。

憑藉著高度發展的馭馬技術而登上世界舞臺的游牧民族,在人類史的漫長跨度中屬於較新的現象。這讓人們能在難以農耕的草原上生產食糧,同時具備擴大人類生活圈的意義。
騎馬游牧民族的誕生
在內亞草原地帶上每年需要移動相當長距離的游牧,其擴散與騎馬技術的普及有著密切的關聯。而這種騎乘技術得等到西元前9世紀左右才被人類掌握。
人類究竟是在何時將馬馴化成家畜仍未有定論,且還存有許多疑點。目前最有力的說法是西元前3500年前後內亞的某處開始食用馬肉,西元前2000年左右西亞一帶開始騎馬,不過作為人類移動的手段,早期更多是以馬拖車。西元前2000年到西元前1500年左右,馬車開始於西亞普及,被當作士兵們乘坐的戰車。戰車與家畜化的馬匹於西元前1400年左右傳至中國。馬匹與戰車的使用讓長距離的軍事行動得以實現,也造成各地王權的統治範圍規模擴大。
騎乘技術的普及較戰車晚了許多。西亞於西元前1000年,內亞草原地帶則於西元前900年之後能證明騎乘馬匹的考古證據才逐漸增加。關於初期游牧文化的早期遺跡(西元前9世紀—前8世紀),咸認以南西伯利亞圖瓦(Tyva)的阿爾然(Arzhan)一號墳為嚆矢,此處出土了許多青銅製的馬銜、馬鑣。所謂的馬銜是穿過馬下顎沒長牙齒空隙部的金屬棒,馬銜兩端露出部分安上鑣,再繫上頰帶防止馬銜掉落,並連結韁繩讓騎手得以控馬。到這個階段人類終於能夠自由統御馬匹了。草原地帶騎馬的人們能憑藉著步行遠不能及的速度進行長距離移動,擴大畜牧的規模與移動距離。至此,騎馬游牧民族於焉誕生。
隨著騎馬游牧民族勢力的擴大,騎馬技術也傳播到歐亞各地。在此過程中騎馬的人們開始手持武器,形成了精悍的騎兵軍團。在不具引擎動力系統的時代,騎兵軍團乃最富機動力的超強軍隊。之後歐亞大陸各地的戰場主角逐漸由戰車部隊轉變為騎兵軍團。伴隨騎乘馬匹的技術革新打造出騎兵軍團,這在世界史上數度發生的軍事革命中稱得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其帶來的結果將如後所述,使騎馬游牧民族於軍事面占得優勢,以此軍事力量為基礎形成了游牧王朝(游牧國家),並進一步席捲歐亞各地。
游牧民族與定居農耕民族的共生關係
憑藉著高度發展的馭馬技術而登上世界舞臺的游牧民族,在人類史的漫長跨度中屬於較新的現象。這讓人們能在難以農耕的草原上生產食糧,同時具備擴大人類生活圈的意義。如此,西元前900年以降內亞便由以北方草原地帶為主的游牧民族及以南方綠洲周邊為主的定居農耕民族,兩大操持不同營生方式的人類集團並存,此狀況更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所謂的游牧是指畜牧的一種形式。使用表示移動的「游」與表示畜牧的「牧」合併而成的詞彙,帶著「移動式的畜牧」之意。亦即帶著綿羊、山羊、馬、牛、駱駝等家畜群隨季節而移動的畜牧形式。配合此種移動生活方式,居住上採用組合式帳篷。個別游牧集團大致都有各自固定的冬、夏草場與移動路線,且通常每年都會進行定期的遷移。
對游牧民族而言,家畜群就是所有的財產。因此,純粹的游牧形式生活能自行生產的物資僅限於家畜,並不足以支撐自給自足的生活。從過往開始,包括穀物、蔬菜等食糧與日用品等物資皆須從外部取得。為此,游牧民族透過交易或掠奪方式,從居住於綠洲等處的定居農耕民族、城市商工居民處獲取。換言之,所謂游牧的生產方式並無法單獨成立,自古便須與定居的農耕民族或都市居民這些他者有所往來。
這樣的說明或許會給人一種自給度低的游牧民族是必須依靠定居農耕民族或都市居民的弱勢群體印象。有一部分的游牧民族確實如此,特別是在游牧生活形式遭邊緣化的19世紀以後更加顯著。但回顧漫長歷史,卻可看到游牧民族占據政治上的優勢,統治綠洲與都市,並頻繁促其上繳稅金與進貢,究其原因,即在於前述以騎兵軍團為靠山的軍事實力。
同時,從綠洲居民的觀點看來,這種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關係也不必然是屈從或被迫,一些時候更是種必需的狀況。例如在內亞的許多綠洲,其可耕地與適合畜牧的草地範圍有限,因此從很早期便開始出現農牧業以外的謀生方式,即以交易為主的營生手段,他們與其他綠洲和區域間存在商隊貿易的發達商業活動。而為了讓商隊貿易能夠順利進行,確保連結綠洲間交通網絡的安全便不可或缺。在游牧民族大範圍軍事力量的庇護下,商隊得以維持長距離交易的安全,也促成歐亞各地間的活潑商業交易。關於這個旁側面向我們也必須加以關注。
內亞史的重要性
內亞對一般人而言仍是陌生的區域,在亞洲史研究領域中,近20餘年來學界才逐漸出現「內亞史」這個歷史研究的框架。內亞原本是1960年代歐洲學者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所提倡的空間概念,而內亞史的歷史研究內容包含蒙古史在內,大多都是由日本研究者推動深耕。
過往無論中國或歐洲定居民族保留下來的傳統歷史敘述,以及西洋成立的近代歷史學論述,都將騎馬游牧民族視為周邊與野蠻,此研究框架的最重要意義,就在於從歷史上重新審視游牧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亦即,以內亞草原地帶的騎馬游牧民族為核心,他們憑藉卓越的騎兵軍事力量於歷史上數度建立游牧王朝,擴大本身版圖進而含括周邊定居農耕民族,重視游牧民族在歐亞各地一直以來推動的歷史進程。一如本書中所舉出的,蒙古帝國可以定位成內亞騎馬游牧民族主導歐亞歷史時期的一個頂點。
此外,如前所述,內亞除了生活於草原上的騎馬游牧民族外,也存在進行農耕與工商業、生活於綠洲的定居人群。因此內亞的歷史是草原的游牧民族與綠洲定居民族兩種相對社會的共生關係結合後,以此為基調展開而來的。而範圍廣大的內亞也因具備種族、語言、宗教等多樣性,所以也才能被視為一個歷史世界來處理。
後述連結內亞內部草原與綠洲,被稱為「絲路」的交通、商業網絡即是支撐著此二者的共生關係而發展起來的。因為有連接廣大內亞的交通、商業網絡,使近代之前被認為各自孤立的歐亞大陸各地區得以藉內亞媒介而相互連通。被定居農耕民族視為邊緣的內亞,在近代之前,特別是海上交通比重增加的16世紀之前,擔任著連結世界樞紐的地位,這在世界史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騎馬游牧民族的集團或王朝憑藉著軍事力量上的優勢涉足此農耕、游牧交界地帶,進一步入侵中國本土……農耕、游牧交界地帶成為連結內亞與中國本土的區塊。
二、游牧與農耕相遇的內亞東方史
華北與內亞的連結
此處暫且擱置內亞,先將本書目光轉向歐亞大陸東部。北至萬里長城以南、西至西藏高原以東、東南臨海,此範圍內指涉著「中國本土」。根據自然地理及生態環境特質可以秦嶺山脈、淮河一線劃分南北,此線大約與年降雨量1000公釐線相互重疊。劃分中國地理區的方法眾多,本書將基於此最簡易的二分法將此線北側稱為華北,南側稱為江南。關於江南的發展留給本系列第二卷細述,此處且略過不提。
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華北年均降雨量大約在400至800公釐,降雨最少處僅約日本四分之一的雨量。此區域不僅降雨量少,而且受到季風的影響降雨偏向集中於夏季至秋季,整年的降雨分布區別明顯。職是之故,此區經常暴露在春、夏的旱災與夏、秋的洪水威脅下。雖然自然環境的條件嚴苛,但自西元前6000年起這塊土地上獨自出現小米、黍的農耕栽培以來,即出現立足於農耕的文明,且在世界史上也屬於知名的早期發展文明。
若從歐亞大陸整體的觀點來看華北區域,它位於內亞的東南邊緣,橫跨在內亞乾燥地帶與東亞濕潤地帶之間,是從乾燥轉向濕潤的地區。華北的西部與北部和內亞在地理上有密切相鄰的關係,華北北部的大同盆地、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一帶標高較高,與戈壁沙漠間夾著蒙古高原,且二者相連,地勢上並無明顯區隔。而長安所在地的關中盆地受與蒙古高原地勢相接的黃土高原所包圍,西側隔著隴山與西藏高原接壤,朝西北方向而去,在祁連山脈北側與散布著綠洲的河西走廊相通。自古即為中國王朝政治中心的關中盆地,位於和內亞鄰接的區域上。
農耕、游牧交界地帶的歷史重要性
地理上分界並不明顯的蒙古高原與華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生態環境區別,毋寧說兩者具備著連續性。華北地區越往西、北降雨量越少,氣溫也越低。華北西北部的氣候特徵與內亞相同,屬於乾燥寒冷的狀態。
這種自然環境的共通性,導致橫跨蒙古高原南側及華北北側的地帶並存著適合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與適合農耕民族生活的可耕地,內亞的游牧民族與中國本土定居的農耕民族雙方都可生活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廣袤延伸。具體而言,即是從大興安嶺東麓經遼河上游、陰山山脈、鄂爾多斯高原,一直連綿到西藏高原東端的帶狀區域。
因應不同時代狀況雖有所變動,但歷史上此一帶狀區域為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頻繁接觸、混雜的空間,因為雙方之間經營交易,此區附近興起與發展了大量城市。此外,騎馬游牧民族的集團或王朝憑藉著軍事力量上的優勢涉足此農耕、游牧交界地帶,進一步入侵中國本土,偶爾甚至出現將其納入統治的時期。農耕、游牧交界地帶成為連結內亞與中國本土的區塊。
關於農耕、游牧交界地帶(也稱為「農牧接壤地帶」)的想法,在日本由妹尾達彥所提倡,之後石見清裕與森安孝夫等人更深入探討,近年被內亞史與中國史相關研究者所接納,其重要性受到廣泛的認可。

此框架也不再使用過往東亞世界論所建構的,以中國文明馬首是瞻形塑而成的世界觀,而是各類種族、人類集團生活的多元化空間,他們擁有各式各樣的語言、營生方式、宗教、習俗等。
何謂歐亞大陸東方史
本書中為了從內亞與中國本土相連接的觀點來思考歷史,將持續以騎馬游牧民族的動向為中心關注內亞史,並與東亞史及中國史相接,嘗試重新設定「歐亞大陸東方」這個空間概念。而在歐亞大陸東方史的框架下,主要以西元4世紀至14世紀這段時期為討論對象,並以來自蒙古高原及其東側滿洲平原(又稱東北平原)之狩獵游牧民族為核心,描繪該些游牧集團(游牧王朝)進入中國本土的趨勢,分析他們給中國或東亞歷史帶來的巨大衝擊。
所謂的歐亞大陸東方史,並非以內亞史或東亞史(抑或中國史)的動向為主軸來審視,而是企圖以更寬廣、平等的視野進行歷史研究的一個框架。當然,意味著「歐洲+亞洲」的歐亞大陸一詞產生自近代歐洲,此地理概念帶著歐洲在前亞洲在後的優勢含意,但此處將站在中立的,強烈意識到內部連結關係的立場,將亞洲與歐洲視為一整塊大陸,並在這層意義上冠以歐亞大陸之名。
歐亞大陸東方指涉的範圍,大致包含帕米爾高原以東、中國本土、朝鮮半島、滿洲、東西伯利亞、蒙古、河西走廊、東突厥斯坦、西藏、雲南、直到中南半島的廣大範圍。亦即不限於中國本土、朝鮮半島等一直以來稱為東亞的區域,還包含內亞東側部分(即北亞與中亞的一部分)及部分東南亞地區。
此框架也不再使用過往東亞世界論所建構的,以中國文明馬首是瞻形塑而成的世界觀,而是各類種族、人類集團生活的多元化空間,他們擁有各式各樣的語言、營生方式、宗教、習俗等。從而,此區域設定雖包含受到源自中國本土、蒙古、滿洲等各地王朝政治、文化強烈影響的地區,但絕無將其視為單一文化圈並與其他區域切割的意圖,因此無須想定一個僵硬的框架。例如,將帕米爾高原區分為東西部的方法,僅是從內亞乾燥地帶連結東西的發想進行思考,不必然有嚴密的區隔。在某些時候也同時考量蒙古和中國本土的發展關係,因此會出現需要跨越東突厥斯坦涵蓋至西突厥斯坦的情況。
根據這種寬鬆且開放的地區概念,方有可能全盤概觀內亞騎馬游牧民族集團、王朝與中國王朝的歷史開展:雙方如何相互對立、交流、融合;游牧王朝如何統合、統治;以中國本土為據點的王朝如何進出內亞等多邊多樣的關係性。從而當我們追溯在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游牧王朝與中國王朝霸權下,周邊各中小型王朝、集團等諸勢力如何存續,嘗試理解內亞史上常態性的政治勢力多元化狀況時,這也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框架。
此外,在描述歐亞大陸東方史時,當然也必須將中國南部至東南亞乃至南亞的海域世界納入考量,不過該部分將留給本系列叢書中專門針對江南發展的第二卷進行討論。此處須先言明,本書除處理蒙古時代的第五章外,基本上都限定在北方的歷史敘述。
中國王朝與馬匹
筆者思考中的歐亞大陸東方史,其基本構造係以蒙古高原、滿洲平原之狩獵游牧與中國本土(華北)農耕此二類相異營生方式為個別基礎,透過探討游牧王朝與中國王朝(中原王朝)兩類型相異之王朝國家如何接壤,強調其間如何興亡消長。
至於在中國本土南方形成的中國王朝,其詳細說明則留給本叢書系列第一卷。此處僅想指出從秦朝至漢朝中國王朝處於成立期階段的幾個統治體制的主要特徵:在歐亞大陸上擁有足堪自豪、首屈一指人口的中國本土農耕社會以其生產力為基礎建構出巨大的官僚組織及常備軍隊;基於發達的公文行政而發展出郡縣制等行政機構;為支持王朝統治由官方制定獨尊儒術的體制性教學制度等。
但是,我們也不能漏看建立中國秦、漢王朝的華北西部位於內亞邊緣上較為乾燥的地區,此自然環境相對容易導入發源於內亞的馬匹繁殖技術。馬偏好乾燥、寒冷的地理環境,討厭暑熱。如「南船北馬」一詞所示,運河、河川、湖沼等水源豐富的江南地區主要交通方式為船隻,而乾燥的華北則多使用馬匹。歷代以華北為根據地的中國王朝,皆無例外的在繁殖、飼養馬匹上投注心力,畢竟擁有強大的騎兵軍事力量是確保王朝存續的重要骨幹。在這點上,位於華北及蒙古高原接壤處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對華北的中國王朝而言,作為一處容易抵達的馬匹產地,具備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可思議的是,西元前3世紀末匈奴與秦朝都在同一時期各自統一了蒙古高原及中國,形塑出游牧王朝與中國王朝兩種類型互異的基本政治型態……
游牧王朝的原型
接著探討關於北方游牧王朝的部分。關於內亞誕生騎馬游牧一事已於前文提及,日後則出現以騎馬游牧民族為主幹的游牧王朝。文獻中能確認最早的游牧王朝是西元前8世紀到西元前4世紀繁榮於黑海北岸與高加索北方,由斯基泰人(Scythians)建立的王朝,在希羅多德(Herodotus)於西元前5世紀以希臘文寫成的《歷史》(Histories)一書中留有翔實的記載。不過,根據最近的考古學成果,顯示西元前9世紀至西元前8世紀時期內亞區域就已經逐漸散播共通的游牧文化,因此可以推論游牧王朝的起源可能位於更東方的蒙古高原西部或者內亞東部。
內亞東部之中,戈壁沙漠以南之南蒙古出現騎馬游牧民族社會,根據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大致出現於西元前7世紀以後,亦即中國春秋時代中後期。關於內亞東部的游牧勢力,中國文獻開始正式記載者為司馬遷的《史記》。根據《史記》,西元前3世紀,自中國戰國時代晚期至秦朝統一天下的這段時間裡,有東胡、匈奴、月氏三股游牧勢力鼎立。其間匈奴出現了英明的君主冒頓單于(前209─前174年在位),他統合了國內的各部落,之後打敗東胡與月氏,歷史上首次統一了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匈奴勢力也擴張到南方的華北方面,利用秦朝滅亡後的混亂入侵中國本土,漢高祖劉邦(前202─前195年在位)出兵征討平城被匈奴困於白登山即為知名歷史事件之一。此時漢朝只能向匈奴求和,大量納貢,結為兄弟關係並採取和親策略。之後漢武帝劉徹(前141─前87年在位)發動對匈奴全面戰爭,雖然付出大量的犧牲卻成功逆轉形勢,南邊的漢朝取得了優勢。
匈奴從君主的單于到他手下的統治者階層、再一直到民眾為止,平時都過著游牧移動的生活,一旦發生戰爭立刻武裝化身為騎兵軍團。其軍事、政治、社會組織採取十、百、千、萬的十進位體系,單于坐鎮於中央,王族配置於左右(東、西)兩翼,任命二十四長擔任隸屬部落的領導者,其麾下依十進位法組成軍事組織,最後形成整個族群的聯合體。觀察所有這些制度即可發現都與之後的鮮卑、突厥、蒙古等游牧王朝共通,也可說早在匈奴的階段即已確立內亞游牧王朝統治體制的基本結構。
歐亞大陸東方史的南北結構
不可思議的是,西元前3世紀末匈奴與秦朝都在同一時期各自統一了蒙古高原及中國,形塑出游牧王朝與中國王朝兩種類型互異的基本政治型態,並於西元前2世紀以後呈現匈奴與漢兩大王朝南北對峙的結構。日後,包含蒙古高原在內的北方游牧王朝對峙以中國本土為據點的中國王朝形成歐亞大陸東方史的基本調性,具體而言可以舉出:6至9世紀的突厥、回紇對隋、唐;10至12世紀的契丹對五代、北宋;12世紀的金對南宋;14到16世紀的蒙古對明朝等。
雖說如此,但僅以游牧王朝與中國王朝的二元對立形勢,並無法說明歐亞大陸東方史。因為有如在反映前述蒙古高原與華北間的生態環境具有連續性一般,我們屢屢可見以北方游牧民族為核心的王朝藉著壓倒性的軍事力,穿越蒙古高原與橫跨華北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南下壓制定居農耕民族,統治中國本土的事例。具體而言,有5世紀以降以鮮卑拓跋氏為核心的北魏,以至於隋、唐時代的一連串王朝(拓跋國家);10世紀以突厥系沙陀集團為核心的五代諸王朝(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至於北宋(初期);10世紀的契丹(遼);12世紀的女真(金);13世紀的蒙古(大元大蒙古國);17世紀的滿洲(大清帝國)等,均以出自游牧集團的軍事力量為核心,不斷應自身王朝所需斟酌取捨漢代以來中國王朝的統治體制,統治部分或全部的中國本土。簡要而言,即中國本土的歷史上頻繁可見多樣化的民族集團,以及狩獵民族、游牧民族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王朝國家進行統治。

歐亞大陸東西方向的拓展
思考歐亞大陸東方史時,除了前述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形成的南北結構之外,東西方向的人、物、資訊移動也非常重要。歐亞大陸內陸的高聳山脈屬東西向延伸,因此在東西方向上沒有自然障礙阻礙交通。只有西方的烏拉山脈與東方的大興安嶺山脈例外,唯此二者皆非十分險峻,不足成為阻止人們移動的障壁。
如前所述,北緯45至50度附近草原地帶(蒙古高原——哈薩克草原—南俄草原)東西連綿延長,自古騎馬游牧民族東西向移動容易。因為是草原地帶的通路,故也稱「草原絲綢之路」(Steppe Route)。同時,其南邊多為更乾燥的不毛之地,藉著山上流下的河水形成綠洲,星羅棋布於廣大的沙漠地帶且發展為綠洲城市或聚落,而自古連結綠洲的交通就十分發達。例如東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位於巨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中央,北邊天山山脈南麓與南邊崑崙山脈北麓散布的綠洲連結成交通網。這些河西走廊綠洲間串接起來的交通路線也連通至中國,日本一般稱為「綠洲絲綢之路」(Oasis Route)。除此之外,對歐亞大陸東方區域而言青海(安多地區)的山間通路及橫斷西藏高原南部的通路也是東西交通的重要道路。
應該注意的是,內亞內陸區域發達的交通讓中國絲綢運往西方,造就眾所皆知,亦即俗稱的「絲綢之路」,然而這個名稱卻太過強調於連結歐亞大陸東西方的側面,實際上內亞交通道路不僅連結東西,也包含了連接北方草原地帶及南方綠洲或者農耕地帶的功能。考量此點,近年已重新將絲綢之路認定為內亞連通東西南北的總體交通網絡。
此內亞的交通網絡與圍繞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路線並列,自古連結歐亞大陸各地,在歷史上一直擔任著要角。從短距離的日常用品交易到以奢侈品為主的中、長距離交易為止,存在各種活絡的貿易與人群移動,各種各樣的語言、宗教、思想、技術也藉此在歐亞大陸的廣大範圍中相互傳播。歐亞大陸東方的歷史留下深刻的文化擴散現象,可舉源自印度的佛教傳播、源於西亞的伊斯蘭教傳播等為例。
此外,歷史上反覆見到的大規模集團移動與王朝興兵的軍事行動、勢力擴張等現象大致都沿著此交通網推動,北方草原地帶自匈奴以降,誕生於內亞東部的強大游牧王朝或集團許多都沿著歐亞大草原地帶擴張或移居至天山以西。具體事例有突厥的向西擴張、契丹(西遼)西遷至突厥斯坦、蒙古空前絕後統合歐亞大陸等。同時,與草原地帶游牧王朝相互呼應,以中國本土為根據地的中國王朝也嘗試涉足東突厥斯坦的綠洲地帶。例如漢朝與唐朝對西域的經營,便都是著眼於對抗匈奴或突厥這些北方游牧王朝的戰略。
套用關注歐亞大陸東方這片廣大區域的歷史區域框架時,不僅可見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定居農耕民族的交互作用,還可將前述歐亞大陸規模的東西交流置於視野之內,藉此得以處理歷史的巨大潮流。本書即使用此種寬廣的觀點,追溯4世紀至14世紀歐亞大陸東方的歷史動向。

延伸閱讀:
渡邊信一郎:在厭中時代,以日本視角重探中國史
丸橋充拓:從江南看中國——一部極具張力的動態史
| 新書快訊 |
| 全套購買 |

1972年生。專研歐亞大陸東方史。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代表著作:《オ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共同撰寫,勉誠出版)、《中国経済史》(共同撰寫,名古屋大学出版会)、《概説中国史》(共同撰寫,昭和堂)、《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共同編著,勉誠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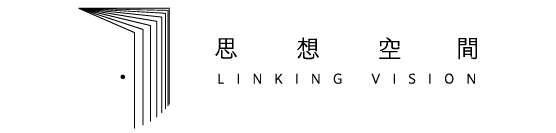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