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怡絜)
(攝影/陳怡絜)
在這個文學作品愈賣愈差的年代,寫文學史不會很寂寞嗎?「有一些老人會看。」紀大偉直覺地回了這麼一句,隨後又補上,「不會啦,還是有一些年輕人。」他手上戴著鮮豔的G-SHOCK電子錶,他說每次挑這樣的錶,店員都會建議他挑一些比較「男生」的顏色,可他偏不,他買了好幾隻顏色豔麗的錶,每天輪流戴。
他寫這本《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也多半有這樣的心情,「從台灣到美國,很多人都建議我不要做同志文學,都說寫這個沒有市場,太不重要了。」所以,寫這本書的紀大偉就跟買錶一樣,才不管是老人還是誰要看,反正恁爸就是要寫,而如果你不關心小說和文學,這本磚頭書也可以當八卦讀。
比如,書中提到50年代的台灣社會新聞,有各種活色生香的同性戀報導,最奇情的可能是「黃效先殺人案」。革命先烈黃百韜的兒子黃效先,殺死同性戀友人並焚屍,因父親對國家有功免去死罪。這則新聞前前後後被報導了半年,死者家中的狗半夜狂吠也寫,黃效先扮女裝入獄也寫,連死者的頭蓋骨也赤裸裸見報。黃效先稱只與死者發生一次性關係,結果法醫檢查他的性器官是否有異常,新聞標題是:「失足僅一次,身體無變態」。
紀大偉說,把八卦的社會新聞放入書中,有二層意義,「小說和報導不盡然是事實,但卻是各種發春、花癡的紀錄。台灣文學和新聞報導都有一大堆偷窺。」這本文學史裡討論的同志文學,不見得是肉身相搏,而是各種飄忽輕渺、gay gay的文本。它談論的不是「主體」,而是「主體效果」,只要聞起來有「gay味」,都算討論的範圍。
所以,黃效先是不是gay,幹過幾次,有沒有穿女裝入監都不是重點,而是眾人八卦他、談論他的方式是什麼。
八卦新聞在此的第二層意義是,「很多人談到同志文學,必說到白先勇的《孽子》(發表於1983年),可是在他之前,難道沒有其他人寫嗎?談白先勇就會說他繼承《紅樓夢》的傳統,可是難道他沒看社會新聞嗎?」紀大偉比對時間點,《聯合報》當年大量報導黃效先命案時,白先勇是高中生,極為可能也沒錯過這場長達半年的八卦風潮。
當然,這不代表《孽子》的內容有多少比例取材自社會新聞,而是出現於這樣時空環境的同志文學,很難擺脫當時社會條件的形塑,文學與真實世界,其實是互相滲透,改造彼此。「《聯合報》創刊頭幾年就大量在寫同性戀新聞,他們不會憑白無故就突然對同性戀感興趣,這和當時美國的氣氛有關。」
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對同性戀社群的壓迫,恐懼像傳染病傳來太平洋這頭,成了一則又一則荒誕獵奇的社會新聞,而獵奇的新聞也成了滋養台灣文學作品的沃土。「很多人認為解嚴後是同志文學的高峰,但我認為在二蔣戒嚴時期,才是最精采的。」
 (攝影/陳怡絜)
(攝影/陳怡絜)
美國是台灣新聞「造妖」的源頭,同時卻也是台灣同志文本裡不斷書寫遙遠的理想之國,好像到了美國,才是同性戀真正「做自己」的時刻,紀大偉也是「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的那一代人,「我本來就是吃西方奶水長大的。大家對多毛巨乳大驚小怪,我看多了。我小時候也覺得去美國就可以吃很多(男體)……但後來發現台灣更方便。」他認為,不自由的年代,苦悶的生活,打砲還要被醫生檢查性器官正不正常,文學成了偷渡的出口,「台灣關於同志的歷史文獻很少,反而是在50年代之後留下大量的同志文學作品。」這是舉世少見,於是書的副標是:「台灣的發明」。
這個另類的「台灣之光」成了紀大偉研究的窗口,他寫同志文學史,更描繪戰後50年代的同志生活和精神樣貌,這是一段特殊的「在地經驗」,「比如,你要研究泰國同性戀,不會研究他們的文學,研究日本同性戀,可能會需要一本二丁目口述歷史,但台灣太特殊了,是同志文學。」
紀大偉以自己為例,大學時因為藝術片常有很多裸男,為了看裸男,他花很多時間在電影上,「可是當你接觸久了,會發現這個圈子可能因為片廠文化等緣故,非常的異性戀氣氛,沒有我立足的地方。可是寫小說,我知道只要我敢寫,很多同性戀的東西可以寫,會寫得跟別人很不一樣。」
沒有電影產業,沒有太多娛樂場所的島上同志們,最後就守著一方電腦(或幾張稿紙)寫寫文章或是和「同好」一起讀讀文學小說,在這種背景下的同志文學,充滿意淫、偷窺和八卦。「可是,有小T跑來問我,台灣有什麼小說是在寫女同志的?現在校園裡很多人已經不知道邱妙津和朱天心了……」同時在政大教授台灣文學的紀大偉有這樣的觀察,文學閱讀在這一代的同志已經不若當年。
「80年代未,邱妙津在書裡立志,要出人頭地,要拿兩大報文學獎。現在如果有人講這個會被笑死,現在小gay不會有人說我要立志寫小說。」同志文學不僅是「台灣的發明」,還是個「期間限定」的台灣發明。文學已不是生活最重要的事了,但如果你不是一個關心文學發展的讀者,這本書仍有具啟發之處。
例如很多人說:同性戀只是愛戀對象跟別人不同,其他都跟一般人沒有兩樣。紀大偉不這樣認為,「同志在很多方面跟主流社會都格格不入,有一套自己的價值。」他們更傾向選擇彈性工時的工作,會花費很多消費在旅行和健身運動。同性戀是一種「生活風格」嗎?「生活風格指的比較是消費面,同性戀在很多生活的選擇都跟別人不一樣,也許因為他們從很小就意識到自己跟社會主流的『時間表』不同,格格不入,就把自己豁出去了。」
 (攝影/陳怡絜)
(攝影/陳怡絜)
幾歲念大學,幾歲結婚生子,幾歲該買房買車,主流社會對人生有一套「時間表」,同志族群的生命時間是在這之外的,而是發展出一套自我的價值標準(例如,35歲以上就可以稱為老同志),那麼,同志的生命時間表指向的未來,是一個怎樣的未來?
紀大偉舉美國同志研究的觀點,「他們說,不要歌頌美好的未來,聽得很煩。同志有很多骯髒的過去也應該回顧,可以歌頌。未來沒人知道,怎麼可能只有更美好?我們也都知道,很多人玩壞掉了,我們都知道啊。」
同志文學史的未來呢?「可能也沒有什麼好寫了,不自由的時代過去了,現在玩樂的花樣太多了,以前我們聊天還會問,最近看了什麼小說?現在的小gay們已經不是這樣,忙著在臉書露肉賣騷就沒時間了。」即便網路鮮肉賣騷隨手可得,可是同志文學寫公園裡口交、三溫暖打砲,社會新聞寫黃效先穿女裝在監獄教大家跳土風舞,凶猛、出汁到味,也沒有在怕誰的。
延伸閱讀
1. 【紀大偉|台灣同志文學簡史SP】50年代《聯合報》的同志奇觀
2. 【專訪】專精嗅聞痛苦的葛奴乙──廖梅璇《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
3. 【專訪】《女子漢》楊隸亞:對我而言,又女又男的狀態可能就是一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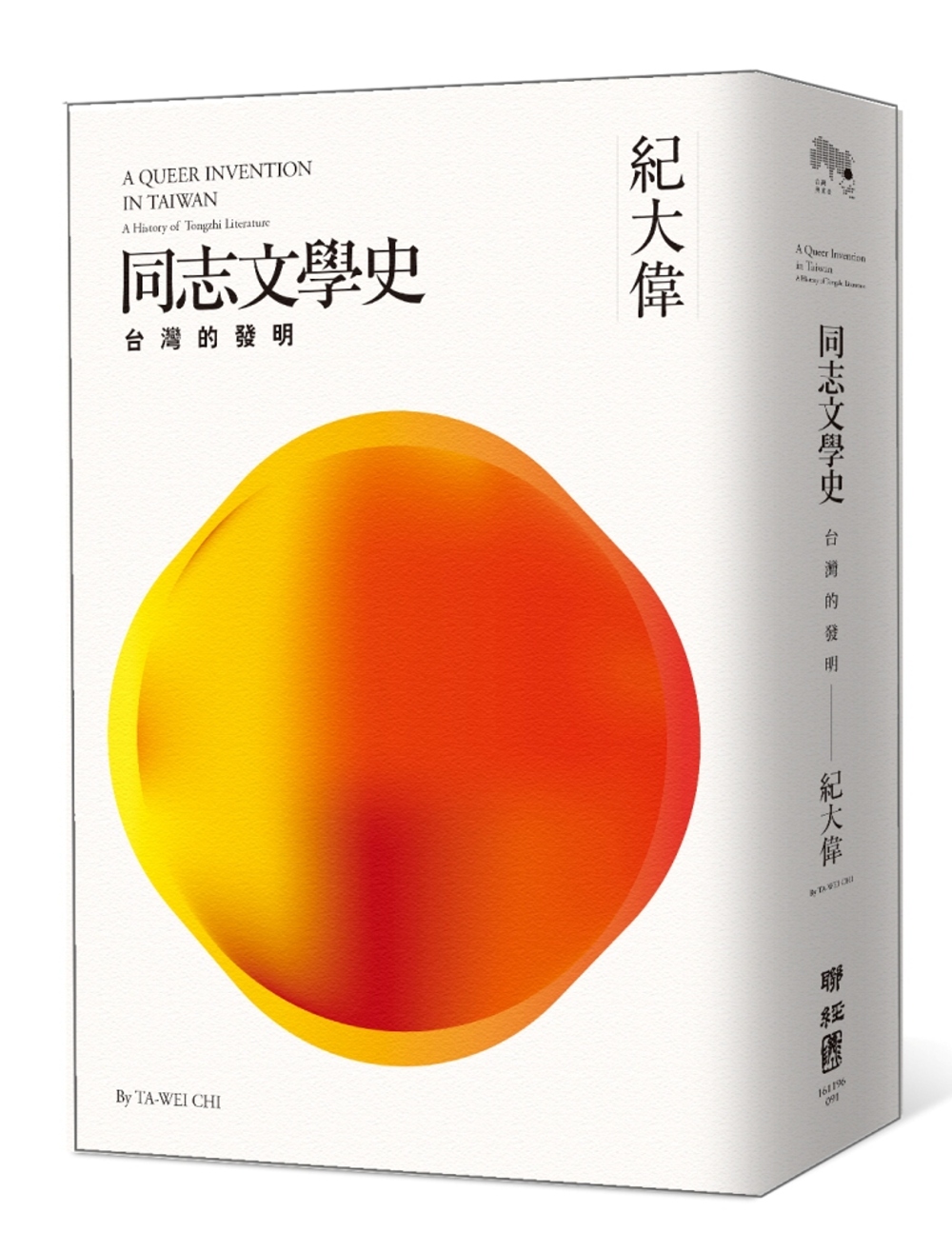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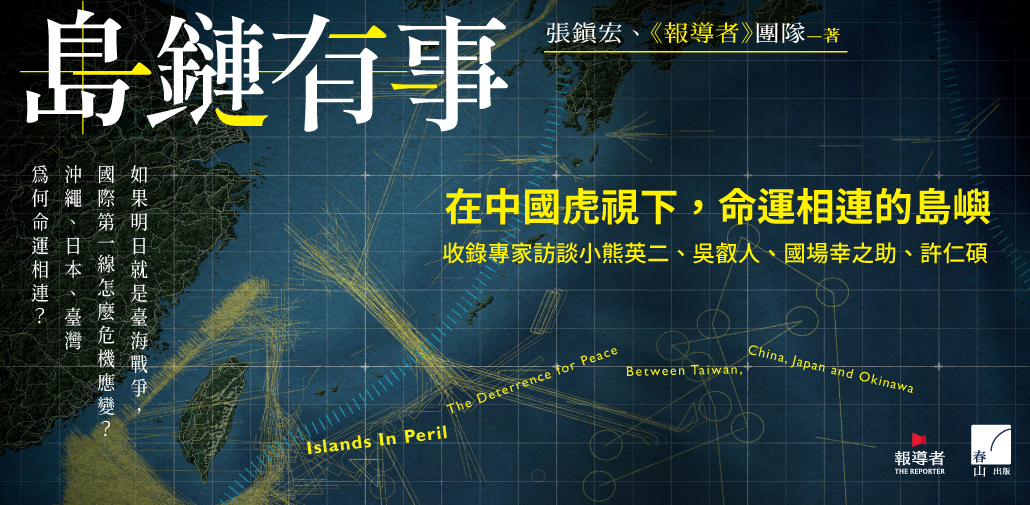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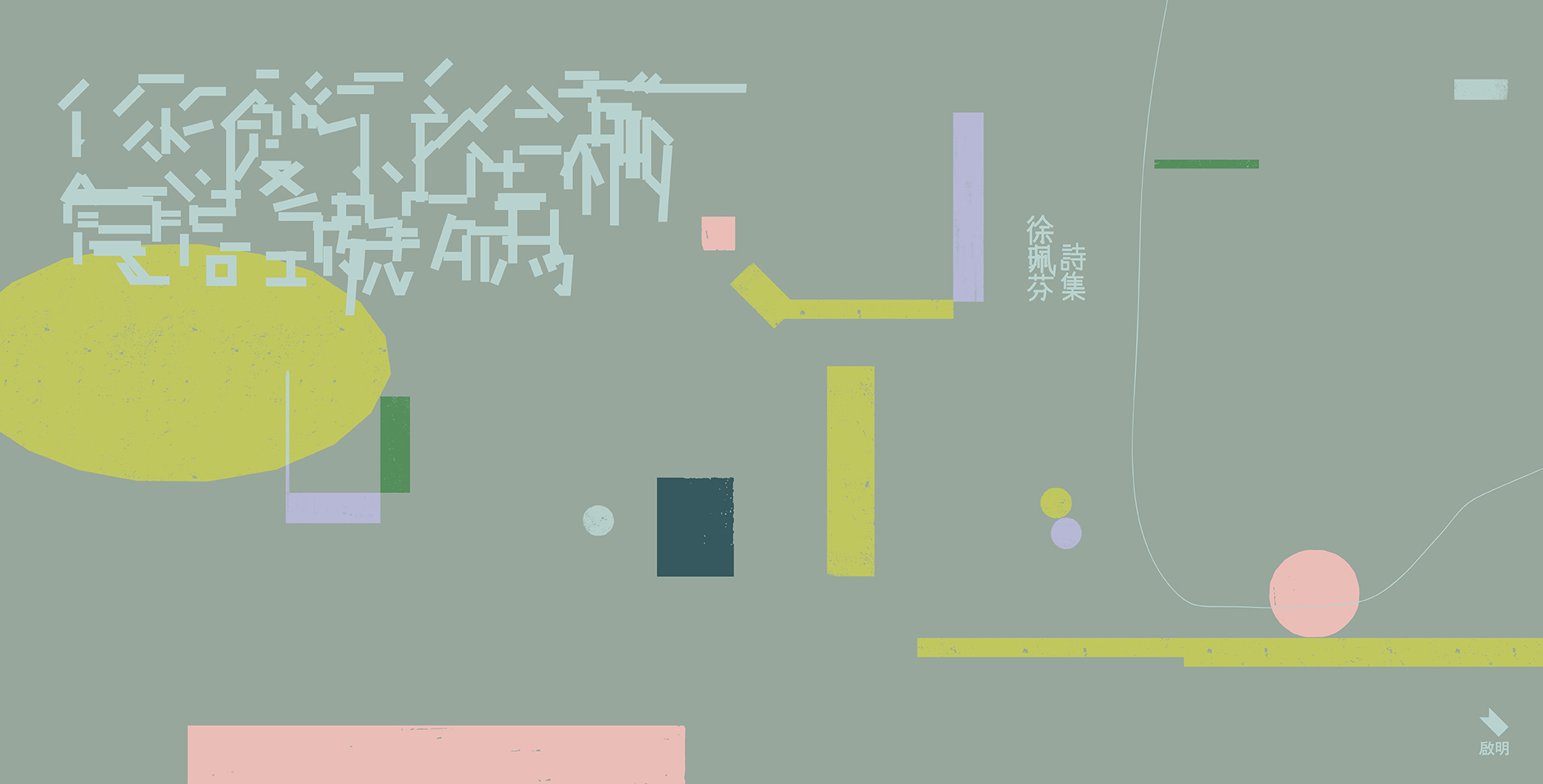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